展覽筆記 vol.2 唐五代定窯「官」款 西安火燒壁窖藏,西安博物館 - Ding Ware 'Official' and 'New Official' Marks, Tang to Five Dynasties Found at 'Huoshaobi', Xi'an Museum
- SACA

- Feb 21, 2024
- 12 min read
Updated: Jul 2, 2025
西安博物館 西安火烧壁窖藏“ 官” 字款唐代白瓷赏析
定窯「官」字款白釉器物一批
1985年西安火燒壁窖藏出土
西安博物館收藏了一批西安北郊出土的窯藏白瓷50余件,其中帶有“官”字款白瓷30件,這批瓷器製作規整,胎體輕薄細膩,釉色白中閃青,其精美程度堪比中國古代白瓷的翹楚之作。
圖片提供:SACA學會讀者一眼千年
窑藏发现
這批瓷器出土於西安市火燒壁東村南部。1985年3月的一天,西安華光勞動服務公司的建築隊在西安火車西站北部施工時,在距地表0.6米處發現一灰色陶罐,內裝瓷器百件,因為陶罐當時已被挖破,罐內的瓷器也多有破碎。經隨後趕到的西安市文管會工作人員清點比較完整的瓷器有52件,其中帶”官“字款的白瓷33件。這批瓷器有3件調撥陝西曆史博物館,其餘均收藏於西安博物館。這批窯藏瓷器中的2件青瓷、盤僅余殘片, 還有1件白瓷瓶同樣僅余足部與口沿的殘片,本文暫不予介紹, 余者皆為碗、盤類圓器,包括“官”字款白瓷、無款白瓷兩大類。
“官”字款白瓷器33件,包括三尖瓣花口盤、五雙脊瓣花口盤、五尖瓣花口盤、五寬瓣花口盤、五寬瓣淺口碗、敞口碗等6種類型。
“官”字款三尖瓣花口盤(圖1),數量最多達17件.口為三瓣花形,尖狀花瓣,花瓣間有凸起狀直線筋脈,口徑11.7釐米。

唐“官”字款三尖瓣花口盤
“官”字款五雙脊瓣花口盤(圖2),盤口為雙脊五花瓣形,口徑14.4釐米。

唐“官”字款五雙脊瓣花口盤
“官”字款五尖瓣花口盤(圖3),盤口為尖狀五瓣花形,口徑13.5釐米。

唐“官”字款五尖瓣花口盤
“官”字款五寬瓣花口盤(圖4),盤口為五寬瓣花形,口徑13.6釐米。

唐“官”字款五寬瓣花口盤
“官”字款五寬瓣淺口碗(圖5),共4件,碗口均為五寬瓣花形,形制相同,大小略異,口徑13.8-21釐米。

唐“官”字款五寬瓣淺口碗
“官”字款敞口碗(圖6),敞口斜直腹,口徑16.8釐米。

唐“官”字款敞口碗
這批“官”字款白瓷製作異常精細,胎體輕薄,形制規整,通體施釉,釉質均勻純淨,釉色純白或白中略泛淡青色,器底外部刻划“官”字款,款識是在施釉後加以刻划,然後再燒制而成。
無款白瓷器17件,包括拍腹花口盤、折腹圓口盤、弧腹敞口盤、壁形足碗4種類型,其中折腹盤9件,數量最多。
折腹花口盤(圖7),敞口折腹圈足,器沿作六缺口花邊,缺口下內壁凸起5道直線為飾。胎白質堅,內外施釉,圈足底與足內無釉,釉白閃青,外壁下邊釉厚,有流釉“淚痕”,呈淡青色。口徑15釐米。

唐折腹花口盤
折腹圓品盤(圖8),敞口折腹,素面。胎白堅硬,釉色白閃青,外壁有明顯修整痕跡和流釉“淚痕”,圈足較寬。口徑15.5釐米。

8 唐折腹圓品盤
8-1 . 俯視圖
弧腹敞口盤(圖9),敞口,弧形壁,圈足較寬.胎白堅硬,釉色閃青.口徑14.3釐米。

唐弧腹敞口盤
璧形足碗(圖10),碗口邊沿凸起,腹較淺.胎白堅硬,瓷化程度高,釉色有兩種,一種白中閃青,一件白釉.外壁均有明顯的輪旋刀痕和流釉痕跡。

唐壁形足碗
這部分無款白瓷器的胎、釉特點與“官”字款風格一致,可以斷定為同一窯口生產但其精細程度明顯遜於同出的“官”字款白瓷。
窖藏“官”字款白瓷窯口歸屬
火燒壁窖藏一經問世就引起業界廣泛關注,其中的“官”字款白瓷更是關注的焦點。“官”字款白瓷在全國各地都有出土,但數量不足10件出土較多的有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出土18件,浙江臨安錢寬墓出土14件,而火燒壁窖藏一次就出土30余件,而且製作精良,造型多樣,數量、品質均堪稱全國之最。
有關“官”款白瓷器的研究,如李輝柄《關於"官""新官"款白瓷產地問題的探討》(《文物》1984年年第12期)、權奎山《關於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問題》(《中國古陶瓷研究》第五“)、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987年年第5卷第2期)等都有專門的論述.對“官”字款白瓷的窯口歸屬,主流觀點認為是北方河北南部定窯生產的精細白瓷.有人根據遼墓出土的白瓷數量相對較多,且赤峰缸瓦窯出土有“官”字款窯具,提出本地區出土的“官”字款白瓷應為遼官窯缸瓦窯生產。但是缸瓦窯並未見“官”字款瓷器出土,是否實際生產過“官”字款瓷器,尚待考古資料的證實。浙江和湖南的考古工作者在當地晚唐至五代墓葬中時常發現有“官”字款瓷器出土,且有些品種比較獨特,比如普遍出土的白瓷盒在其他地區較少發現,據此推斷這些白瓷的產地或為本地出產。但至今未在江浙地區找到晚唐五代精細白瓷的生產窯址,專家們還是傾向於浙江、湖南地區的“官”字款白瓷大部分還是北方的定窯系產品。
雖然近年來河北南部的井陘窯、內丘邢窯窯址陸續也發現有“官”字款白瓷殘件,但出土數量最大的還是定窯。截至1999年,“官”與“新官”字款白瓷在定密遺址出土約30余件,還有“會稽”“定”等款識,與全國南北各地的墓葬及塔基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器的胎、釉特徵有一定的共性,所以從產地判斷,“官”字款白瓷主要還是由定窯生產。
定瓷以燒制白瓷著稱,是繼唐代邢窯白瓷之後興起的一大瓷窯體系,位居宋代五代名窯“柴、汝、官、哥、定”之列,主要產地在河北曲陽縣,曲陽縣在唐代時期歸定州管轄,故稱定窯。定窯白瓷以造型纖細典雅、釉色純淨明麗著稱於世,歷來為文人雅士所推崇,也受到瓷器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關注。20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葉麟趾先生首次確認定窯遺址位於河北曲陽澗磁村,得到了業內人士的廣泛認同.新中國成立後,分別於1960年、1965年年、2009年三次對窯址進行了科學發掘,根據考古調查與窯址發掘出土情況與地層疊壓關係看,確定定窯創燒於中、晚唐時期,五代時得到迅速發展,北宋時期是定窯白瓷的全盛時代,直到元代末期定窯瓷器才停止規模生產。
創燒初始的定窯以燒制、黃釉、黃綠釉瓷、以及單純粗陋的器物為主,僅有少量白瓷。定窯窯址早期堆積層出土的典型器物、匣鉢、窯爐與邢窯遺址的相同或相近,可以看出定窯在發展初期借鑒、吸收了邢窯的工藝技術。
邢窯位於河北臨城、內丘兩縣境內,北距曲陽澗磁村160公里,是唐代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窯場,與當時名揚天下的越窯青瓷齊名,時稱“南青北白“。由於地理位置的接近,定窯受邢窯影響很大,又得益於曲陽靈山盆地豐富的瓷土和釉料資源,善於學習和創新的定窯工匠在唐代末期已經能燒造胎釉質量俱佳的精細白瓷。
唐末五代澗磁村窯址的堆積層中白瓷數量大增,瓷器的胎、釉質量都大為提高,其中的精細白瓷胎質輕薄,胎質潔白細膩,般不再施化妝土,通體施釉,釉層均勻稀薄,釉色白中泛青,足底刮削露胎,碗類多外捲成唇口,盤類多仿金銀器的造型做成花瓣口。這一時期的定窯白瓷以華美的花式造型和潔淨瑩潤的素釉取勝,燒造方法是採用一匣一器的仰燒法,為了使坯體避免與窯具粘合,其間以石英砂墊隔,因而燒成後在器物的底部近釉處往往粘有石英砂粒,這是早期定窯的一個特徵.這一時期由於是以木柴為燃料,並在還原氣氛中燒成的,因此它的白度很高,還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定窯時發現五代時期燒還原焰的窯址一座,經對早期定窯進行分光反射率與透光度計測結果證明“唐後期及五代的定窯白瓷是用還原焰燒成,北宋和金代的白瓷是用氧化焰燒成,故白瓷的呈色有明顯的差別。
北宋時期是定窯白瓷的創新與大發展階段,具有獨特風格.定窯此時為了提高產量,創造性地採用覆燒工藝,剔、划花裝飾工藝得到廣泛應用,釉色從前期的純白或白中閃青轉變為白或白中泛黃,精細的胎釉燒造水平已達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燒造工藝的改變,使北宋的定窯瓷器帶有芒口、刻划花等鮮明的時代特徵.1960年年在定窯遺址北宋地層考古發掘出土了外底刻“尚食局”的所謂龍鳳盤,說明在北宋時期定窯已經為宮廷燒造器物,躋身宋代五大名窯之列.澗磁村北的山巒里還發現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瓷器商人趙仙重鐫)五代馬夔的碑刻,記錄了北宋時期定窯制瓷業的盛況。
金元時期是定窯瓷器的衰落階段,地方誌記載北宋末期“靖康之變”後,定窯以兵燹廢.考古資料證明,金、元時期定窯並未停燒,依然有一定的生產規模,但是燒制質量比較粗陋,多為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器具,到元代末期定窯瓷器才逐步停燒。
西安火燒壁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器形仿金銀器皿的花式造型,胎壁輕薄,精巧細膩,釉色純白微微閃青,僅足端刮削露胎,可見少量粘沙痕跡,符合早期定窯白瓷一匣一器正燒法的產品特徵:尚未出現代表獨特風格的北宋定窯白瓷的刻划花裝飾, 以及因覆燒工藝的應用出現的芒口現象。可以確定, 火燒壁窖藏瓷器是定窯早期也即唐末五代時期的產品, 它們與定窯遺址出土的白釉唇口碗(圖11)、“新官"款花品瓷盤(圖12)並無二致。

白釉唇口碗

新官"款花品瓷盤定窯遺址出土
紀年墓出土“官”字款白瓷
“官”與“新官”款白瓷在遼寧、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均有出土,據1999年的考古資料統計,全國各地共發現唐代晚期至北宋晚期“官”“新官”款白瓷計有169件,這些瓷器雖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窯燒造,但絕大多數當為定窯生產.我們選取具有斷代意義的紀年墓予以分析.需要說明的是,火燒壁窖藏“官”字款白瓷主要為碗、盤兩類,所以我們也選取紀年墓出土的圓器予以比對,琢器暫不涉及。
紀年墓資料顯示,最早的“官”字款白瓷器出土於浙江臨安晚唐時期錢寬墓(唐光化三年,900年),出土15件精細白瓷,其中10件花口盤均有“官”“新官”款。隨後又發掘了錢寬夫人水邱氏(卒於901年)墓,出土了17件白瓷碗、盤,其中3件有“官”字款,11件有“新官”款.赤峰大營子遼駙馬贈衛國王墓(遼應歷九年,959年)出土花式鑲金口足“官”字款白瓷盤2件、花式“官”字款白瓷大碗2件.最晚的“官”字款白瓷器出土於遼寧朝陽耿延毅夫婦墓(遼開泰九年,1020年),出土“官”字款蓋罐1件。可以看出,“官”與“新官”款白瓷流行於晚唐至北宋早期約120年的時間里。
北方“官”字款白瓷有不少出自塔基,比較著名的有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瓷器115件幾乎全部是北宋早期的產品,許多瓷器在器底刻有“官”字款,具有北宋定窯的獨特風格,有掩飾芒口的金銀鑲飾,有刻划花裝飾,這與火燒壁以釉色取勝的純淨、素雅風格迥異。
另外需要提及的紀年墓是吳大和五年(933年)墓,此墓)出土白瓷器14件,其中有底足沾有砂粒的花瓣口白瓷盤4件、三瓣花式白瓷碟1件、大白瓷碗1件。這幾件白瓷器雖然並末標識“官”字款,但與西安火燒壁出土的白瓷器在造型上相似度很高,對火燒壁窖藏瓷器的斷代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筆者觀察大和五年墓出土的白瓷,發現其光潔度相對不足,應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實際生產年限很可能偏早數年。
將西安火燒壁窖藏出土的“官”字款白瓷與紀年墓、塔基的出土物比對分析,相似度最高的是晚唐時期浙江錢寬墓(900)年)出土的五花瓣口盤(圖13),其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新官”款白瓷扣銀花口盤(圖14)、“新官“款白瓷碗(圖15),以及吳大和五年墓出土的三瓣花式白瓷碟(圖16)。由此可以確定火燒壁“官”字款白瓷的時代在唐末至五代偏早期。

13.唐白釉花口盤900年錢寬墓出土 / 14.唐末 水邱氏墓土“新官”款白瓷扣銀花口盤 / 15.唐末 水邱氏墓出土“新官”款白瓷碗

三瓣花式白釉碟 五代吳大和年(933年)墓出土
“官”字款分析
關於瓷器上“官”字的涵義目前說法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是指官窯,“官”是官府機構光祿寺“下屬的”太官署“的簡稱;另一種觀點認為“官”“新官”是“官樣”“新官樣”的省寫,均為收取實物稅的標準實物樣。
筆者認為,“官”字款瓷器是皇宮或各級官府向窯場專門訂燒之器.北宋以前並未有“官窯”之說,宮中或官府用瓷多為“官搭民燒”或者官府白營監燒。“官”“新官”款代表一種標識,署有這類款的瓷器就是官方認可的供官方徵用瓷器參考所應達到的最起碼標準質量的器物。從出土“官”字款白瓷紀年墓葬看,墓主都是皇親國戚,或者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權貴.如浙江臨安晚唐錢寬墓及其夫人水邱氏墓,均出土有“官”字款白瓷,墓主錢寬是吳越王錢之父;赤峰大營子遼駙馬贈衛國王墓出土花式鑲金口足“官”字款白瓷盤等,墓主屬於皇親貴戚;河北靜志寺塔基出土許多刻有“官”字款的瓷器,當是宮里或官府禮佛時供奉佛祖的珍貴物品。
因“官”字款瓷器為官府訂燒之器,不計成本,只要精工細作,所以“官”與“新官”款白瓷均是造型規整、胎質輕薄細膩、釉色瑩潤的精細瓷器.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定窯燒造的民用粗瓷,在各時代的瓷片堆積層里所佔比例巨大,並且在周邊墓葬與遺址中屢有出土,顯示定窯一直是以商品生產為主的民窯窯口,“官”字款白瓷僅是官府向定窯訂燒的高端精品白瓷。
窖藏的具體地點與時代
火燒壁窖藏瓷器的出土地點位於唐長安城的安定坊遺址.安定坊位於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從北第一坊為安定坊,據“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東南隅,千福寺,本章懷太子宅,咸亨四年捨宅立為寺西南隅,福林寺,其地本隋律藏寺:東北隅,五通觀.隋開皇八年為道士焦子順所立,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守進宅.“窖藏的出土地點是火燒壁東村南,地處唐代安定坊的東側偏南部,與史籍記載的唐千福寺位置相近,依此推斷這批窖藏或與唐千福寺有關。
千福寺本為武則天之子李賢即章懷太子的府邸,咸享四年(673年)捨宅為寺.)唐代佛教興盛,長安各坊均置佛寺,自皇帝、達官顯貴直至百姓無不信佛、崇佛,捐獻田宅家業供奉佛祖,著名的法門寺地宮珍寶就是唐王室迎供佛祖靚獻的皇家寶藏。火燒壁“官”字款白瓷或是作為珍貴寶物供奉給千福寺.後在唐末戰亂長安城遭破壞,寺院僧眾避禍外逃時匆忙將這些瓷器埋藏地下,希望世道太平之時折返取用.孰知自此天涯淪落歸期無望,這些寶物也從此靜置地下千餘年,一朝出世就驚艷了世人。
火燒壁出土的白瓷埋藏時間不應晚於唐代末期.唐玄宗天寶年間發生了“安史之亂“,國勢由盛轉衰。特別是唐代晚期社會矛盾激化,朝廷內部南北二司爭鬥不斷,權力日盛的地方節度使擁兵自重,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唐長安城出現多次劫難:廣明二年(881年)年)黃巢率起義軍攻入長安,唐僖宗逃往成都,長安城遭遇空前劫難;乾寧二年(895年)因河中節度使繼任之爭,節度使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地起兵打長安,與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互相割據混戰,唐昭宗逃奔終南山;乾寧三年李茂貞藉口朝廷對鳳翔用兵,又率兵攻長安,唐昭宗出逃華州.尤其是天祐元年(904年)朱溫(全)忠)迫使昭宗遷都洛陽,並拆毀長安宮室及民房以營建洛陽,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據“舊唐書·昭宗紀“載:“(朱)全忠率師屯河中,遺)牙將冠彥卿奉表請東駕遷都洛陽.全忠令長安居人按籍遷居,徹屋自渭河而下,連薨號哭,月余不息。“唐末的數次戰亂使長安城屢遭破壞,幾成廢墟。這批瓷器是在朱溫對長安城徹屋遷居之際被埋於地下,時間不會晚於公元905年。
南宋窖藏:重庆荣昌出土瓷器
江苏金坛元青花罐盛银器窖藏
金鱼村窖两处窖藏,共出土龙泉窑瓷器402件,震惊全国文物圈!
元明窖藏、墓葬出土“官哥”窑器若干问题的探索——从繁昌窖藏出土的贯耳瓶谈起
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高安元代窖藏
版权声明:本文来源于 《收藏》作者 李喜萍
Summary of Xi’an Museum’s Huoshaobi Cache of “官 Guan”-Marked Tang White Porcelain
In March 1985, a construction crew north of Xi’an West Railway Station unearthed a buried grey pottery jar at a depth of 0.6 m containing over 100 ceramic fragments. Archaeologists recovered 52 largely intact pieces—33 of which bear the carved character “官” (guan, “official”) on the glaze, while 17 are unmarked. Three marked pieces were sent to the Shaanxi History Museum; the remainder are now in the Xi’an Museum.
“官”-marked Wares (33 pieces)These fine white-glazed porcelain items fall into six shapes:
Three-lobed flower-rim plates (17 pieces, Ø 11.7 cm)
Five double-ridge petals plates (Ø 14.4 cm)
Five pointed-petal plates (Ø 13.5 cm)
Five broad-petal plates (Ø 13.6 cm)
Five broad-petal shallow bowls (4 pieces, Ø 13.8–21 cm)
Straight-rim bowls (Ø 16.8 cm)
All are wheel-thrown with exceptionally thin, delicate bodies and an even, snowy-white glaze tinged pale blue. The “官” inscription was incised into the glaze before firing.
Unmarked Wares (17 pieces)
These include everted flower-rim plates, round rim plates, curved-wall plates, and ring-foot bowls. They share the same kiln characteristics—fine white body, uniform glaze, occasional “teardrop” drips—but display slightly coarser execution.
Kiln Attribution and Dating
Styl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ttribute both the marked and unmarked pieces to the early Ding kiln (Quyang, Hebei) during the late Tang–Five Dynasties period (c. 900–930 CE). Similar “官”‐marked wares appear in contemporary tombs of high-ranking figures (e.g., the 900 CE Qian Kuan tomb in Lin’an), confirming a production date around the turn of the 10th century.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官” Mark
Rather than denoting a state-run “official kiln,” the “官” mark likely signified government-commissioned luxury porcelain meeting a mandated quality standard—used by imperial relatives, aristocrats, and in major Buddhist temples. The high craftsmanship, varied flower-rim forms, and occasional gold or silver mountings underscore their ceremonial or courtly role.
Burial Context
The cache was interred at the site of Tang-period Qianfu Temple (est. 673 CE) in Chang’an’s An Ding Fang district, probably hidden during the city’s turmoil in the early 10th century. Rediscovered in 1985, these rare wares provide invaluable insight into late Tang official patronage of Ding kiln porcel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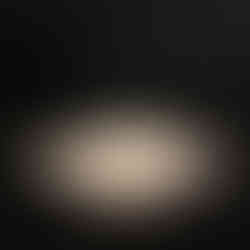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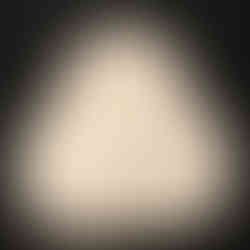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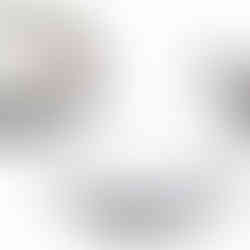
























Comments